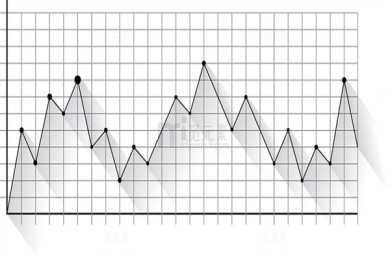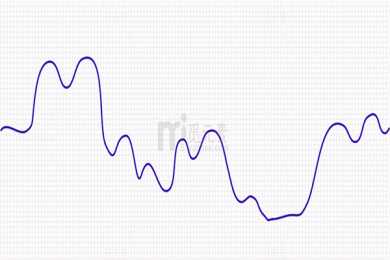小小说:猴爷琐事
小小说:
猴爷琐事
檀香居士
猴爷闭上了眼睛,永远离开了他眷恋的土地和亲人们。
猴爷走时78岁,在鸡冠庄村民眼里看来,也算是高寿而善终。邻居们都说这是他行善积德修来的福分。
位于鲁南山区的鸡冠庄,邱姓是个大姓。邱家上几代都是地主出身,财大气粗,家底殷实。到了猴爷这辈,由于时代变革,加上连年兵荒马乱,已经家道中落,仅剩良田十几亩。年轻时的猴爷,人长得很魁梧,四方大脸,有模有样。不到20岁就娶上了媳妇。媳妇娘家姓王,也出自大户人家,她知书达理,孝敬公婆,贤惠能干,还是鸡冠庄村长的干女儿呢。
按说在这样的家庭里,郎才女貌,门当户对的,自然会其乐融融,令人羡慕。可不知道猴爷哪根筋出了问题,不去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,仗着家大业大,偏偏不思进取、吃喝玩乐,不好好过日子。整天招呼三朋四友,推牌九,下馆子,逢酒必醉,惹是生非。喝醉酒老老实实回家睡觉也就罢了,可他偏偏有个怪癖,那就是酗酒后喜欢打老婆。搁现在说法就是有家庭暴力倾向。刚开始老婆没在意,认为他喝醉酒了发酒疯,不去和他计较。谁知时间长了,家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。
猴爷每次醉酒后都对王氏拳脚相加,老伤未愈,新伤又至,经常打得她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。王氏不能说,不能道,只能以泪洗面。待到次日醒酒后,猴爷认为闯祸了,就赶紧爬起来陪笑脸认错。不是磕头,就是跺脚,对天发誓,拍胸脯、下保证,痛哭涕零地表示要戒酒,正干,好好和老婆过日子,弄得王氏也没法,每次只能暗自叹息,不计前嫌,期待下一次奇迹出现。以后每逢有朋友来喊猴爷出去喝酒时,王氏都不让他去,可猴爷性子豪爽,讲义气,重朋友,感觉若不去赴宴会驳了朋友面子,让人耻笑,所以一直不好意思张口拒绝。王氏也没法,总是拧不过猴爷的驴脾气。去之前总是千叮嘱,万交代:“去就去吧,那就少喝点酒哈!”可每次回来猴爷又都是喝得酩酊大醉,令王氏愈加感到失望,简直无可救药。
因为经常酗酒,导致猴爷的性格越来越暴躁,整天不务正业,家中良田也被倒卖的差不多了,基本上也所剩无几。王氏整天好言相劝,让他远离那些狐朋狗友,做点小本生意以便补贴家用。谁知猴爷对此不屑一顾,越听越烦。在一次酒后,王氏又劝阻他时,长期憋在内心深处的一股怒火终于集中迸发了。猴爷就找茬吵架,越吵越气,吵着吵着,又按住王氏狠狠地毒打。这一次下手太狠了,拳脚、棍棒相加,如雨点般砸在她弱小的身躯上。棍子打断了,拳头打累了,猴爷借着酒劲又拿来铁钳子,用劲狠狠地扭她的胳膊和双腿,疼得王氏如杀猪般嚎叫,顿时惨叫声响彻了大半个村庄。猴爷酒后六亲不认,谁来拉架就骂谁闲管事,邻居谁也劝不住,这一骂,也就更没人敢来拉架了。
这一次暴打过程断断续续折腾了两个多小时,直打得王氏遍体鳞伤,青一片,紫一片,没有一处好地方。她悲痛欲绝,声嘶力竭,泪眼哭干,想去小村子东头水库跳河寻死,怎奈被打得没有一丝力气,连自杀的。走投无路之际,她披头散发,光着脚丫一瘸一拐地跑到村长家求救。老干爹一看,把闺女打成如此惨状,这还了得,再不制止马上就要出人命了,赶紧报官吧。当公社治安员匆忙赶来准备处理这事时,一看猴爷神志不清,舌根僵硬,都喝成这样子了,人家也不好按程序办理,只好又交给村长处置。
老村长也感到左右为难,一边是自己的干闺女,一边是自己庄上的老亲世邻,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,打他一顿也解决不了问题,如何做到一碗水端平,忒难办了。他狠狠地吧唧了几口旱烟袋,眉头紧锁,不断地唉声叹气,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来。无奈之下,只好征求干女儿的意见。这边,村长老婆已经给王氏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,穿上了一双新鞋,头发也梳理得整洁起来。只是她的两眼肿得跟灯泡一般,精神萎靡不振,恰似刚刚受过大刑的犯人。遭受精神和肉体双重摧残的她,已处于是伤心透底,欲哭无泪的状态。
“娃,你干爹没本事,治不了这小子,对不住你呀。是好是歹你说句话吧!”干爹哭丧着脸,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王氏只好点了点头,似笑非笑,捂着嘴,顷刻间又有几滴眼泪夺眶而出。“干爹,您也看到了。这气俺也忍了,罪也受了,这都是命哇!给他多次机会改正,可他就是死不悔改,整天介还是喝醉酒照死里揍俺。再这样下去,俺非得让他给折磨死不可。这个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!”说着说着,王氏浑身颤抖着,又依在干娘的肩膀上哇哇大哭起来。
“孩子,要是能过就在一块凑合着过,不能过就赶紧离(婚)!”她干娘倒是干净利落,也在一旁跟着帮腔。
“俺受够罪了!非离婚不行!”王氏大声咆哮起来,忍受多年家暴,终于下了要和猴爷离婚的决心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,乡下农村信息闭塞,农民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。离婚在当时还是个新鲜事物,一般家庭夫妻关系即使再不和,但凡有一点办法,只要能凑乎着过,男女双方是轻易不敢言离婚的。因为,夫妻俩一旦离婚,总感觉有辱风化,走在大街上最容易被人在后面戳脊梁骨的。
醒了酒的猴爷,发毒誓也没人听了。头磕得再响也没人理睬了。托人给王氏说情,希望她能回心转意,这一次,王氏横下一条心,没有再给他机会。猴爷和王氏注定此生无缘在一起生活了,只能选择离婚。办离婚手续后,王氏回到娘家暂住。没多久,经媒人撮合,远嫁到八、九十里开外的邻县,彻底离开了令她悲痛欲绝的鸡冠庄。新郎虽是个三十多岁的光棍,地地道道的庄稼汉,但人很老实,知冷知热的,对她很好,而且也没啥不良嗜好。对于一个二婚的老半货子来说,夫君不打她,知道过日子,王氏也就非常知足了。
看到王氏如此决绝,猴爷叫天天不应,喊地地不灵,怨天尤人也没用,谁也帮不了他,只能自作自受。本指望过几年再托人给说个老婆,安安稳稳过日子。可酗酒、打老婆的坏名声已经传播方圆几十里,令猴爷声名狼藉,羞愧不已。在面壁思过几个月之后,他酒也忌掉了,烟也不抽了。离婚后,酒肉朋友也不来找他了。只剩下他和年迈的老娘在一起过日子。就这样,猴爷短暂的幸福生活告一段落。他悉心照顾老母亲颐养天年,几年之后无疾而终。自此之后,他孤苦伶仃,形单影只,打了近四十年的光棍。
文革期间,村长见他改掉了游手好闲的毛病,踏踏实实出力干活,也不偷奸耍滑。就摒弃前嫌,安排他常年看护村子里的果园、瓜棚,工分照常拿,这让猴爷感激不尽,做人做事更加老实本分,尽职尽责。鸡冠庄上的老少爷们也逐渐对他刮目相看。与年轻时相比,简直判若两人。由于整天风餐露宿的,吃饭、休息没规律,身子骨受到很大影响,抵抗力逐渐下降。在一次淋雨感冒发烧后,带起了支气管发炎,就落下了永久的哮喘病,农村老家俗称“齁巴子”。村上的孩子们自打记事起,就知晓猴爷有这个老毛病。喘病经常复发,需要常年吃好几种药,药性以辛温为主,导致其皮肤发暗、牙齿发黄,人也逐渐消瘦。村里人又给他起了个绰号叫“赖猴”。
村里小孩上瓜地偷瓜时,如果被他发现,咋呼喊叫,穷追不舍时,只要淘气地叫喊他这个外号,他就立马止步,坐在地上呼呼大喘,好像哮喘病真犯了似的。几个小伙伴就赶紧回来给他捶背,小心翼翼把他搀扶起来。随后自觉地把偷摘的香瓜、脆瓜都如数归还。看到瓜果失而复得,避免了遭到村长训斥,猴爷立马就笑了,而且笑得很慈祥,眼睛眯成一条缝。可能是他一辈子无儿无女的缘故,每逢见到小孩子总会有一种亲切感。他总会轻柔地抚摸着几个小孩的脑袋瓜,像变戏法似得,从窝棚床头的铁盒子里掏出几块冰糖塞到几个小孩的嘴里,几个小伙伴们齐刷刷道一声谢,一阵欢呼雀跃,欢天喜地,蹦蹦跳跳地回家吃饭去了。
村上的老少爷们没有因为猴爷离过婚,就歧视他。因为猴爷早年上过几年私塾,在村子里也算个文化人,字写得很好看,而且人缘也不错。村子里每逢遇到红白喜事,都爱请他当执笔先生,记记账,写写划划,这些都是他的强项。对此,猴爷也乐此不彼,逢叫必到。他性格耿直,坚持正义,帮忙主家处理诸多琐事也比较公道、公平,让人叹服,在村子里很受人尊重。自此,村里人不再叫他“赖猴”,加之辈份比较高,都尊称他为“猴爷”。
但是,家里没有男劳力,就是个不完美的家庭,必须实行重组。为了儿女考虑,刘氏打算再婚了。经过几个月的观察筛选,最终相中了猴爷,作为下半生的依靠。刘氏选择猴爷作为半路夫妻也是经过慎重考虑,最终才下的决定。女儿跟随她来到夫家,儿子还跟着他奶奶生活呢,她总是放心不下,改嫁在一个村子里多少还能顺便照顾幼小的儿子,为前夫家留下血脉,就是改嫁也没人说三道四。
重新组合家庭后,猴爷仿佛又年轻了许多,各方面抓得更紧了。他感觉自己年龄也不算太大,还能出点力挣钱养家糊口。就每天起早贪黑,拾掇地里农活。白天跟村里人上山起石头,卖给水泥厂,赚取生活费。又让村长帮忙承包了几亩荒山,全部栽种上花椒、蜜桃、麦黄杏、核桃等果树,空闲地里全部点上了花生。用挣来的闲钱买了几只山羊让玲妮去放养,一年下来粗略算算,也能收入个两、三万元。比一般的家庭还宽裕呢。刘氏母女俩跟着猴爷吃喝不愁,穿戴不缺,也算享上了清福。猴爷待玲妮如同己出,甚是疼爱,好吃好穿供着她。玲妮也整天围着他爹长爹短地叫着,直乐得猴爷合不拢嘴。
转眼间,玲妮已经20多岁,到了该出嫁的年龄。这要搁在正常女孩子,一般是不愁找到婆家的,可像她这样条件的谁愿意要啊?猴爷老两口为此犯了愁,整天为此愁得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。托人介绍了几家婚事,男方都嫌玲妮傻不拉几的,都没相中。夫妻俩就放下了这事,心的话能养几年是几年吧,只要老两口在,就不能让玲妮受苦。你还别说,世间事,就怕凑巧。也许应验了“姻缘早定”“佳偶天成”那几句话,不觉之间,还真有人上门主动来提亲了。
对方是个老青年,姓马,叫马壮,家在附近村子,人很老实淳朴,父母早早去世,兄妹好几个。因家庭成分不好,近四十岁光景,还一直打着光棍儿。猴爷通过反复打听,综合考察,认为这“小伙子”还行,玲妮跟着他不会受气。即使家里暂时穷点倒不怕,日子都是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,只要人正干就行,于是和刘氏商量后,就同意了他们的婚事。马壮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,他认为傻点就傻点吧,能娶个屋里人给做饭吃、做个伴就不错了。就这样,双方一拍即合,玲妮的婚事就算正式定了下来。
猴爷不光自己结了婚,几年之后又风风光光把女儿嫁出去了。这又成了鸡冠庄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,都说这人不简单。玲妮出嫁这天,猴爷专门花钱让专业师傅给她化了妆,全身上下装扮一新,一点也看不出异样神情。又从城里花钱觅来了几辆奥迪轿车,聘请了专业录像师和摄影师全程记录婚礼过程。陪送的嫁妆也很高档,大橱小柜,五铺六盖,冰箱、彩电、摩托车、洗衣机这四大件,样样都是名牌。
酒席办了四十桌,村里的老少爷们挨家挨户都被请去吃喜酒。猴爷说了,他是吃百家饭过来的,现在也该回请大家一次了,喜礼一概不收。猴爷嫁女,义薄云天,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,一时间在鸡冠庄上津津乐道,被传为美谈,也成为了村里的重磅新闻。他也绝没想到,打发“闺女”出嫁,本来是很自然的一件事。但就是因为做了这件善事,自己的晚年也有了着落,会完全依靠玲妮一家人来孝顺和照顾。按农村人的话说,猴爷得了她这个“闺女”的济。
农村人常说:“傻人有傻福”,“宁可生瞎身,不能生瞎命”,这在玲妮身上得到了最好验证。婚后第二年,玲妮生了个大胖小子,取名来恩,学名马飚,一家人皆大欢喜。由于玲妮弱智,怕遗传给孩子,老两口也没敢让她给孩子喂奶,于是就主动承担起照看外孙子的职责。奶粉净捡质量好的买,衣服也专挑选好看的穿,把孩子打发得干干净净、白白胖胖。老两口拿孩子疼得没法说,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孙子一样,含在嘴里怕化了,捧在手上怕掉了。马壮跟着包工头在建筑队干瓦工,一天能挣个五六十块钱,玲妮也学会了骑三轮车和炒菜做饭,智商也在慢慢提高,或许是爱的感召力吧。每当逢年过节的,马壮一家人准备了鸡鱼肉蛋等物品,装了满满一三轮车车,前来看望老人,直乐得猴爷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看到这个大家庭如此和睦相处,其乐融融的,让左邻右舍们都羡慕不已。
老村长活了九十多岁终于安然去世。送殡这天,她的干女儿王氏带着一家男女老少十余口人前来奔丧。负责外柜的执笔先生正是猴爷,也自然能见到她,当时猴爷想躲也躲不了,想藏也无处可藏。曾经的夫妻四十年后再度相逢,彼此第一眼都认出了对方,当四目相对时,心情是复杂的,只能默默无语。猴爷惊愕地当时就站起来了,手里握着毛笔不知所措。只见他眼里满是忏悔,似有乞求谅解之意,王氏也是泪眼婆娑,点头含笑,似乎已不再记他的仇。处于这个场合下,他们又不能说话问候,好在一起来的年轻人都不认识猴爷,庄上的年轻人也不认识王氏,也都没在意他们之间的眼神交流,否则场面会更加难堪。在外人看来,起身相迎,这只不过是猴爷欢迎客人的一种习惯罢了。
上完帐之后,猴爷又仔细端详了王氏几眼,只见六十多岁的她红光满面,满头银发,彰显富态,听她言谈举止得知目前已经儿孙绕膝,四世同堂了。反观猴爷辛辛苦苦一辈子,家业没有了,原配媳妇离婚了,孤苦伶仃打了半辈子光棍,目前只有一个外孙,还不是亲生的。命运真会捉弄人啊!如此之大的剧烈反差,令猴爷无地从容,恨不得寻个地缝钻进去。他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岁的光景,那时的他,桀骜不驯,天马行空。年轻时造的孽,犯的错,伤害的人,一幕幕、一件件都浮现在眼前……历史仿佛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,令他神情颓废,五味泛陈,一时无法接受现实。对王氏犯下的错,欠下的债,即使下辈子做牛做马也偿还不清。据说事后,猴爷在家里不吃不喝足足睡了三天,才慢慢缓过神来。这也成了猴爷心中永远的痛。
经过老两口的细心照料,外孙子马飚已长大成人,转眼间初中毕业了,据说学习成绩还不错,准备考市内一所重点高中。猴爷因常年患病吃药,身体逐渐垮了下来。马飚自小就很懂事,放学后做完作业,就推着三轮车拉姥爷去看病打针,让猴爷很是欣慰。尽管猴爷和玲妮母子没有任何血缘关系,但通过近二十年的朝夕相处,互相照顾、互相依附,相处融洽,让他们融合在一起,已经有了亲情,真正成为了一家人。一大家五口人,居然有四个姓氏,是这种浓浓深情促使他们紧紧地依偎融合在一起,在村里人看来,这种组合简直无法想象,都赞叹猴爷靠人格魅力创造了人间奇迹。
猴爷的葬礼,在他去世三天之后举行。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自发前去吊唁祭拜,年轻的后辈们依次行礼磕头。村里人,有钱的出钱,有力的出力,各司其职,各负其责。旗啰萨萨,吹吹打打,风风光光,整个葬礼朴实而又不失庄严肃穆。马壮披麻戴孝,马飚打幡带路,整个葬礼的费用几乎都是闺女婿一人掏的。玲妮弱智不会哭爹,马壮就在喇叭匠子中花二百块钱觅了一个哭棺的,代替她行路祭。三拜九叩,有板有眼,连说带唱,悲痛欲绝,“闺女”围着猴爷的柏木棺材,转了一圈又一圈。抑扬顿挫的琵琶伴奏琴声夹杂着凄凉悲哀的哭腔,让前来围观的人群跟着不停地擦泪,都感叹猴爷这一辈子活得不容易,死后能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,也算是非常值得了。
猴爷的一生是悲壮的,又是幸运的。前半生坎坷曲折,后半生安享幸福,先苦后甜,整体上比较圆满。在他身上,全村人明白了“积善人家,必有余庆”这个道理,村里人也会沿着猴爷的足迹,一路遵循,传播千秋万代。
愿猴爷在天堂里继续行善积德,福泽众生。(此文先后被多家网站及媒体转载)
作者简介:贾方团,男,汉族。籍贯山东枣庄,生于上世纪70年代。笔名檀香居士,抱犊雄风,多家报刊特约记者,中国乡土文学作家,山东省枣庄市作家协会会员。毕业于山东滨州医学院临床系,基层副主任医师职称。199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现供职枣庄市山亭区卫生健康系统,为第十届山亭区政协常委,中国农工民主党山亭区支部副主委,兼职于山亭区文联主席团、山亭区作家协会及诗词联赋家协会。
先后在“学习强国”学习平台、《中国红十字报》《健康报》《齐鲁晚报》《》《山东工人报》《农村大众》《枣庄广播电视报》及《山东林业》《运河》文学杂志、《抱犊》文学杂志、《健康山东》《枣庄通讯》等国内众多报刊杂志及文学刊物上发表散文、诗歌、小说、人物通讯等作品220余篇,共计30余万字。荣立枣庄市卫生系统三等功一次。文学作品屡次在全国各级报刊杂志及征文大赛中获奖,荣获健康报征文三等奖,《怀念父亲》荣获2015年度中华情全国诗歌散文作品大赛银奖。